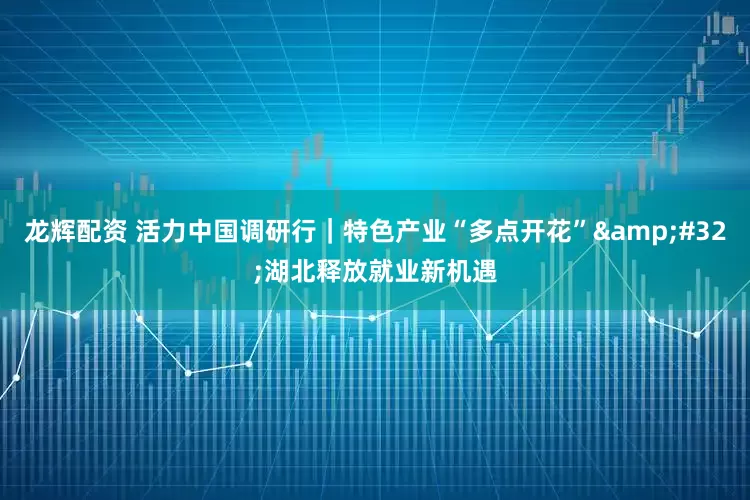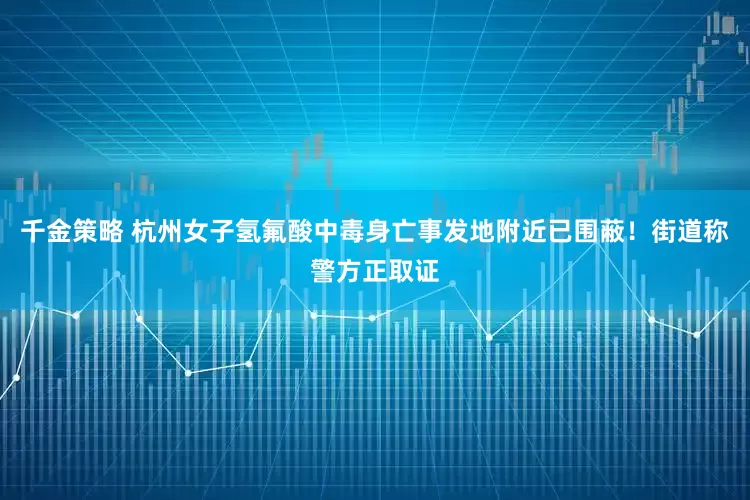1939年6月的一天午后,贺龙拍着马鬃笑道:“主席,这匹铁青乌龙驹六六配资,可不是一般货色!”
延安的骄阳烘得黄土冒烟,毛泽东顺手扯了根青草递到那匹高头大马嘴边,大青马打了个响鼻,把草甩到一旁。毛泽东没有惊讶,只是摸了摸自己身边的小青马,那匹个头不高却极其温顺的川马,此时安静地低头嚼草,仿佛一切与它无关。老主席喜欢小青马,这是警卫员们早就心照不宣的事——稳、不折腾、能长途跋涉,这才合他的脾气。
在延安,骑马并非浪漫,而是一件跟穿布鞋一样日常的工具活。汽车少得可怜,马就成了“战地吉普”。不过毛泽东更多时候还是喜欢自己走路,布鞋踩在疙里疙瘩的黄土路上,累了就拄根木棍。赶时间才上马,他要的是安全和稳定,不求拉风。小黄马死后,办公厅淘来两匹川马,一青一红,跑起来像船在水面滑,一点颠簸都没有。小青马从那天起成了他的“座驾”,小红马则交给了周恩来。

贺龙的到来打破了这份平静。湘西人性情直爽六六配资,他嫌小青马“寒酸”,便把自己最钟爱的座骑牵来了:乌鬃垂肩、尾巴扫地、四蹄踏尘,活像一块打磨到极致的墨玉。纸面资料里常说“良驹识英雄”,可眼前这位“英雄”却瞄了主人一眼后直接甩头,显然谁也不服。毛泽东拍拍马背,笑着感谢贺龙的好意:“你这宝贝怕要骂人哟。”
本来事情就要如此收场,没想到江青横空杀出。她生在山东,后来混迹舞台,骨子里有股“要闹就闹大点”的劲。一眼见到大青马就挪不开步,拽着毛泽东非要留下。新婚燕尔,毛泽东也不好扫兴,加上贺龙盛情难却,铁青乌龙驹便留在了枣园马厩。江青亲自上阵,花了半个月,硬是把这团烈火压成了顺从,她骑马的照片被苏方记者抓拍,黄土高坡上一抹深青,成了许多人眼里延安最飒的一幅画。

照片热乎劲未退,祸事来了。7月中旬,周恩来自重庆回延安述职,毛泽东忙得脚不着地,便让他代去中央党校讲课。江青一听也想去凑热闹,毛泽东点头:既能打招呼,又能学点理论。于是周恩来骑小红马、江青骑大青马,警卫员王来音和蒋泽民跟随。
党校在桥儿沟六六配资,路不算远,却坑洼连连。江青嫌队伍步子慢,突然策马猛冲。大青马撒开四蹄,如箭离弦;小红马被尘土呛得直立嘶鸣,周恩来被甩了出去。人在半空,他只来得及护头,右小臂着地发出清脆的裂响。等警卫员赶到,他额头汗珠滚落,却咬牙说“没事,先把课上了”。医生简单包扎,他便带伤讲完马列。讲台下掌声雷动,只有站得最近的刘久洲看到他袖口不断渗出的血痕。
延安医疗条件有限,骨折拍不了片,只能靠手感复位上石膏。可粉碎性骨折本就复杂,三周后石膏拆除,肘关节已经变形。说来讽刺,周恩来还安慰旁人:“伤的是手,不是脑子。”而我读到这里,总觉得那句玩笑里透着辛酸——一个整日跟时间赛跑的人突然被迫放慢,很难不苦。

邓颖超从重庆赶回来时,救护车坏在西安,她毫不犹豫改乘卡车。到延安已是深夜,她握着丈夫那条弯曲僵硬的手臂,眼圈泛红。就在同一天,毛泽东叫来江青,语气很重:“骑马不是演戏,出了事谁担得起?”江青低头不语,往后好些天都躲在窑洞里不敢露面。
延安总医院束手无策,毛泽东干脆决定:送苏联。既能治病,又能处理对外联络,“两全其美”。国民党竟罕见配合,派出专机护送周、邓赴苏。莫斯科的外科医师切除移位骨块,再辅以电疗、矿泉浴,终于把那条弯不直的手臂救回了一部分功能,能弯曲四十五度。周恩来写信回来,特意一句:“主席,切莫责怪江青。”

而延安的马厩悄悄换了主人。大青马被送给警卫营做通信勤务,小青马仍旧跟着毛泽东,上高原,下窑洞,步子稳健。有人问他为何偏爱这匹个头不高的小东西,他只淡淡答:“走远路,要踏实的脚。”一句话,道尽领袖对人、对马、对事业的选择标准——能“出死力”固然好,但若不守规矩,终究还是隐患。
说到这里,不得不感慨,马是外在的坐骑,性子却映出人的内里。毛泽东沉着,小青马温顺;江青急躁,大青马烈烈;周恩来不喜张扬,小红马低调耐劳。延安岁月里,人和马书写的故事无数,这一桩虽不算战场厮杀,却让后来者明白:在烽火岁月里,每一次看似寻常的选择,都能牵动战友的安危,甚至影响未来的战局。
东启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